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初现曙光,包括湖北省在内的每日新增确诊病患大幅减少,痊愈出院的患者数则大幅增加。而在另一条“战线”上,虽然科学界声音和科普文章不断涌现,但在各种微信群中,继续沉渣泛滥着新冠病毒是生物战或人工制造等各种说法,既有隐晦地继续声称该病毒不可能经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帖子,也包括公开地声讨在《柳叶刀》杂志联名发声反对阴谋论的科学家是为了“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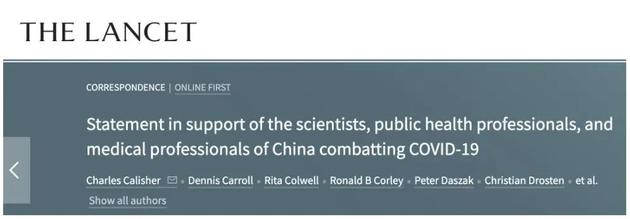 2020年2月19日,来自27个国家的知名科学家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联合声明 | THE LANCET
2020年2月19日,来自27个国家的知名科学家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联合声明 | THE LANCET阴谋论实在层出不穷,每到疫情和重大灾难时总会涌现。在社交媒体主导传播的后媒体时代,它就更容易得到火力支持。同时,它也是一系列社会心理机制的产物。探究这些机制,与驳斥阴谋论同样重要。
新冠病毒人工造?
虽然诸多科普文章已经对阴谋论进行了驳斥,在探讨造成各种阴谋论滥觞之前,仍有必要简单总结下此次有关疫情的各种阴谋论的具体说法,以作为我们讨论滋生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土壤的基础。
最早的阴谋论说法与以往的非典病毒外国造以及转基因是外国基因战并无多大不同,对此进行驳斥的科普文章也很早就出现。很明显,虽然针对不同人群的基因特质的确可能会有不同的疾病感染或发生路径,但这种理论可能性要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且不说作为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绝不会被文明国家轻易践踏,而且生理人口并不等同于国家人口这一点,也让基因战全无可能。美国的华裔人口高达380万,亚裔人口则达到1700万,何况病毒如何变异根本就不可控也不可预测,有谁会冒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可能性来“投毒”呢?
与以往造谣转基因是共济会控制世界的诡计这种很Low的阴谋论相比,这次疫情中愈演愈烈的阴谋论实际上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其一是有了更多“理论依据”,一本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成为了阴谋论者自豪的凭据,虽然该书主编、已经退休的第四军医大学原教授徐德忠只是质疑非典病毒源于自然很困难,且并没有提出任何非自然起源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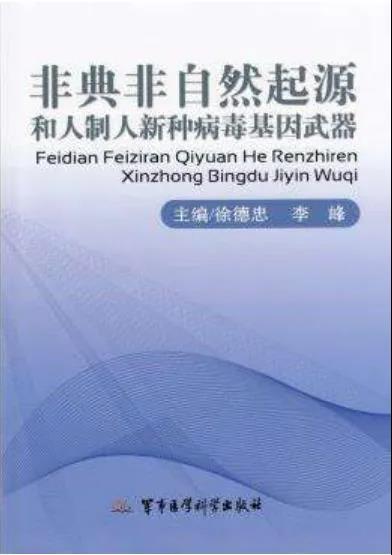 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成为了阴谋论者自豪的凭据
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成为了阴谋论者自豪的凭据实际上,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的团队2017年在云南一个山洞中发现的一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天然基因库,相当于用事实作为反证驳斥了徐德忠等人的猜想。然而,恰恰是石正丽参与的另一项“减毒版人造SARS病毒”的研究,又成为了此轮阴谋论最持久的焦点,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重点。
在全球科学家和中国全国公众被新冠病毒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印度科学家也来添乱,他们贴出预印本论文表示,用于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的关键基因结构,插入了HIV基因片段,这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暗示是人造病毒。
 印度科学家暗示用于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的关键基因结构插入了HIV基因片段 | 图虫创意
印度科学家暗示用于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的关键基因结构插入了HIV基因片段 | 图虫创意印度科学家的这篇神文,让新冠病毒阴谋论的爱好者迅速扩展到国际,不但社交媒体上爱好者众,连美国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Tom Cotton也加入了合唱。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Cotton对武汉病毒的P4实验室可能病毒外泄的谣言“煽风点火”,称该实验室距离首批大量病例聚集地的海鲜市场仅“几英里远”(其实隔着长江,远着呢)。
阴谋论的聚焦
对于驳斥阴谋论,国内外科学界可以算得上积极。除了上面提到的科普文章和在《柳叶刀》上的联名社论外,在各种会议上科学家也踊跃发言。在最近我参加的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华盛顿大学Fred Hutch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Trevor Bedford博士明确驳斥了印度论文映射新冠病毒可能并非自然演化的结论,指出新冠病毒目前的结构完全可能源自自然界的随机进化过程。相反,我们倒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冠状病毒中的这些片段是来自艾滋病毒,更不要说是人工组装的了。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人工组装 | 图虫创意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人工组装 | 图虫创意在主流科学家的一致驳斥下,印度科学家的论文也从bioRxiv生物论文预印本网站上被撤下(不同于已发表论文撤稿,从预印本网站上撤下文章,不需要什么程序和声明),无疑,生产这样的文章来蹭热点,会对这些印度科学家的声誉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在支持新冠病毒人工造的人看来,徐德忠教授则显得更加形象高大了。微信中转发的帖子,更是经常要把徐教授的著作拿来说事。当然,限于他老人家的年资,国内估计也没有什么知名学者愿意出来驳斥,何况他的非典病毒人工造的说法,因为不是发表在同行评议的论文上,也谈不上撤稿。
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石正丽研究员所参与的构建“减毒版SARS病毒”(SHC014)用于研究病毒演化规律的研究,则成为了众矢之的。网络的指责,则从早期的该病毒可能不慎外流,同时演变成中国一些极端网民认为的美国基因战武器库、以及上述的美版阴谋论的“新冠病毒中国造”,其后还加上了武汉病毒所领导出售实验动物牟利导致病毒外泄这一荒诞不经却也引发媒体追逐的版本。
而随后学者们从病毒基因测序和演变规律做出的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早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传染病大爆发这一结论,又让诸多阴谋论的说法多了一份扑朔迷离。
 学者们从病毒基因测序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早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传染病大爆发 | 生命日报
学者们从病毒基因测序和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早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传染病大爆发 | 生命日报新冠病毒不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在去年12月初华南海鲜市场感染事件之前存在当然有可能。但这与阴谋论者所声称的新冠病毒人工造却八竿子也打不着。在病毒从原始宿主蝙蝠到传染到人类之间的中间宿主的缺环,可以让科学家合理的推测病毒传播的时间,而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将新冠肺炎的传染病源头定位于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是一种疾控策略,是基于我们具有的明确科学证据来追溯源头和控制传染源。这种基于现有证据的应用手段,本来就不会排斥通过更多科学证据来进一步追踪病毒人间演化的路径。
阴谋论的心理基础
既然阴谋论的说辞其实禁不住逻辑的推敲,为何在每次疫情袭击时,它总会大行其道呢?这就要从经历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公共事件后人们的心理状况来分析。
在我最近参加的AAAS年会上,网络谣言与阴谋论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Emma Spiro指出,在经历重大的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或接受的危机事件时,普通人本能地要通过各种说法来寻找意义。虽然这位心理学家用的数据是2013年波士顿恐袭,但用来说明突然打乱我们现有生活的新冠疫情,显然同样合适。对于普通人来讲,实在难以理解科学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还会突然出现这种难以控制、难以溯源的大规模感染。
 在经历重大的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或接受的危机事件时,普通人本能地要通过各种说法来寻找意义 | 图虫创意
在经历重大的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或接受的危机事件时,普通人本能地要通过各种说法来寻找意义 | 图虫创意既然要寻找意义,为何不能顺着科学家一步步的科研进展顺藤摸瓜呢?不是这些科学家的工作太末节了,而是因为人类的风险感知往往不是理性驱动的。
美国著名风险心理学家Paul Slovic曾在1987年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探讨人们的风险感知。他提出了驱动人们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一个是风险事件的悲惨程度,另一个是人们对其不熟悉的程度。因而,人们对车祸这种人们更容易碰到、更加熟悉的灾难的风险感,就低于人们对民航空难的风险感,更低于比民航空难发生概率低几个数量级的核电站事故的风险感。而实际上,有统计表明,民航空难造成的死伤,还远低于人们驱车去机场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伤亡。
近年来,Slovic还进一步提出,悲惨事件对人们风险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抽象的统计数字。
 悲惨事件对人们风险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抽象的统计数字 | Pixabay
悲惨事件对人们风险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抽象的统计数字 | Pixabay这样的风险感知应用到疫情时人们的心理表现时,其结果就是人们对疫情风险感的空前提升,因而也就更加需要寻求一个意义。而此时,另外的风险感知机制就要发挥作用了。这些机制,首先就是我在本人“科学传播的科普”专栏中反复提及的负面倾向。
人们在进化过程中要格外关注负面信息才能更容易摆脱风险。所以他们会无视科学家针对新冠病毒取得的持续科研进展,而更加关注悲惨的特例。
与此同时,人们面对风险并不是积极广泛地搜集证据得出理性结论,而往往会因为一些早期的特定信息形成思维框架,然后反复把新获得的各种提示性信息与这些成行的框架进行快速比较得出结论,这也强化自己早先的判断。而阴谋论说辞对人们的影响恰恰让这些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
面对无法理解的灾难,人们要急需寻找一个解释。阴谋论和其他谣言等负面信息迅速填补了这种需要,当阴谋论的一些要素构成了人们的思维框架后,他们就快速地应用这种框架来解释新获取的信息。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 图虫创意
很多科普文章虽然在第一时间就会驳斥阴谋论,但它们提供的信息往往进不了笃信者的脑子 | 图虫创意这其实与转基因现象有很大可比性。当10年前转基因争议因为安全证书的颁发被大量负面报道迅速推进公众话语空间时,人们难以理解政府居然要推进这种被媒体和反转控们声称为有风险的技术,于是阴谋论说辞就乘虚而入,至今也没有完全消歇。
当然上述的风险感知机制并非都是坏事。政府的疾控工作也要利用这些因素来迅速调动人们共同防疫。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却对它们的心理机制研究不足,在利用风险感知因素时,并不能很好地区分积极的结果和笃信阴谋论这种消极行为。
心理与社会因素的互动
我们前面介绍的心理机制,其实在学界也一直被诟病,其一是它们往往是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的机制,其二是认知框架形成后,难道正面信息真的就无孔可入了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心理机制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来分析。
首先从负面角度讲,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极大地放大了负面信息。其实早在互联网成为人们主要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前,Slovic就注意到政客之间的攻讦让媒体更容易放大负面信息。在微信时代,负面信息提供者从占人口数量极少的政客扩展到很多公众号作者甚至是一条普通帖子的撰写者,这种效应自然会被不断放大。
 微信时代,媒体更容易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会被不断放大 | Pixabay
微信时代,媒体更容易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会被不断放大 | Pixabay在后媒体时代,众人都是知识生产者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实很多受过一定科学训练、了解一些科学界内情的人,会克服他们在传统媒体时代被边缘化的状况,突然因为他们能提供特定信息而成为信息源或信息中心。
包括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内的正面信息提供者当然一直在努力,他们也当然会影响很多人。实际上传统媒体基本上不会报道任何阴谋论。但除了后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无处落地(因为人们压根不看一篇网上转的文章是否来自传统媒体)外,另外的一些心理机制也在帮助阴谋论的支持者和笃信者。
这又都是一些什么机制呢?首先是信任;其次是信任往往要附着在人们感知到的道德基础上;第三则是感知到的信息权威性。这些机制与上述的风险感知因素造成的后果,最终共同聚焦到了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上。
在中国,无疑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但那是对抽象的科学家。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的研究就表明,人们在转基因问题上对科学家的信任,就显著低于对抽象的科学家的信任。其次是道德感知,转基因就不说了,这次处于风口浪尖的武汉病毒所及其P4实验室,不断被造谣者拿出来当靶子,而每一次矛头一定会关涉到道德判断,像所长资历不佳、管理违规、卖实验动物、科学狂人(指石正丽研究员团队四处不顾危险来寻找载毒蝙蝠)等,通通被倾倒到病毒所身上。其结果,就是虽然一些造谣水平极低的阴谋论说辞(如卖实验动物牟利)可能会被人们抵制,但普通人即便抵制了这些低级谣言,仍然会觉得这个科研机构哪里不对劲儿。
 石正丽研究员团队不顾危险寻找载毒蝙蝠 | 一席
石正丽研究员团队不顾危险寻找载毒蝙蝠 | 一席另一个近年来国际科学传播界关注极高,但在国内却没有什么研究的心理机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动机性推理。也就是人们在获取科学、风险信息时,往往选择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那些信息。在国外这一点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与特朗普当选前后西方政治极化态势相关。不要以为中国就没有这种极化趋势,只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分析罢了。
回到我们的议题,虽然科学家和科普人士早就出来驳斥帝国主义投毒这种阴谋论说法,但各种官方辟谣平台上,尽管把喝酒防新冠这种调侃都当成了谣言来辟,却错过了生物战阴谋论的大谣言。这不能不放大了这方面的心理趋势。
还是我的老家内蒙警方动了真格的,把一位造谣新冠病毒是美帝生物战的网民直接拘留,霎时起到了震慑作用。既然直接的生物战“不让说”了,那些不会被封杀的、攻击病毒所科研人员参与外方阴谋的帖子,在风险感陡升、造谣者活跃、能满足人们动机性推理(既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道德感知)等诸多信息涌现等因素推动下,自然也就大行其道了。
应对之道
既然如此,那该如何应对呢?首先要承认,这方面国内外的研究是严重不足的。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何以在重大事件后阴谋论如何横行。针对社交媒体的阴谋论或谣言传播研究,更多是用大数据印证和拓展了既有结论,而不是从行为干涉角度着眼来破解阴谋论传播。
所以,探讨应对,我们更多还是从实践经验结合各种心理机制提出一些建议。首先当然是科研机构自身的研究和行为过硬。包括管理、晋升等各种平常完全是家务事的内部行为,在危机关头都会成为阴谋论和谣言风起的噱头。
 科研机构自身的研究和行为要过硬 | 图虫创意
科研机构自身的研究和行为要过硬 | 图虫创意但这些维系科研的道德行为的举措,并不能被公众所感知。他们所感知到的,往往是疫情等危机爆发后被爆出的或者造谣出来的不当举动。这就要求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研机构真要把科学传播当成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举措来做。人们对科学家取得的成果,往往赋予了道德意义。一个机构积极投身科普的科学家越多,影响越大,人们对其的道德赞许往往也较多。这方面的道理很简单,人们看科研进展的新闻,大多数人其实不是因为对科学多奇妙的兴趣,而是因为相信这种进展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收益。相信这种未来收益本身,就意味着对科学家要信任。
但这个前提是人们要知道这些成果。你从来不报道,或者只是把何人何时发表了何等牛逼论文做成了新闻标题,然后把论文摘要变成中文构成新闻内容,指望公众因此对你赋予了道德信任,这恐怕是不现实的。
除此之外,科学家传播能力的培训,包括危机公关情况下如何发声、如何交流,这些都应该成为科学家常规训练的内容。在传统媒体时代一个机构可以只培训一两位发言人,但在后媒体时代,至少一个机构的科研主力,都应该获得这些方面的基本技能或熟知相关的求助路径。“用生命来担保”这种话,其实对破解科学阴谋论毫无裨益,因为“用生命来担保”这句话所具有的道德特征,需要依附在科学家被道德化构建的前提上。而阴谋论已经破解了这种前提。
这些是长线建设。亡羊补牢其时未完,但眼下如何办呢?要论述科学的危机公关,恐怕又要一篇文章的篇幅。此处其实可以用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那就是雇佣社会上的优秀危机公关机构,与他们一起工作,虚心学习他们的技巧,同时坦诚、认真和开放地帮助公关专家们提升对科学界的理解,以及共同拓展对人们面对风险信息的心态的理解。
当然,其实科研机构雇佣外部专家,甚至使用经常被妖魔化的“公关”这个词本身也意味着长线建设。但破解科学阴谋论本身就是一个长线工作,需要整个科学传播体制做出相应调整。
